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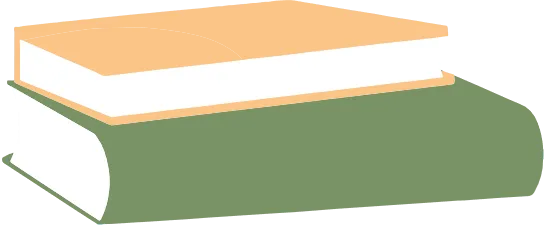
錢穆先生作為我國近現代著名的歷史學家,其代表作《國史大綱》是抗日戰爭戰火中各個大學通用的歷史教科書,詳于闡述經濟、政治、社會、文化、制度,對于具體的人與事則一略而過。而《中國歷代政治得失》可以說是《國史大綱》的進一步延伸,通過對中國古代漢、唐、宋、明、清等五個朝代政治制度的深入分析和比較,試圖揭示政治制度背后的邏輯和規律,以及對中國社會發展的深遠影響。“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”,國浩深圳合伙人李芳對此書進行了細讀,并摘其精要,與大家共享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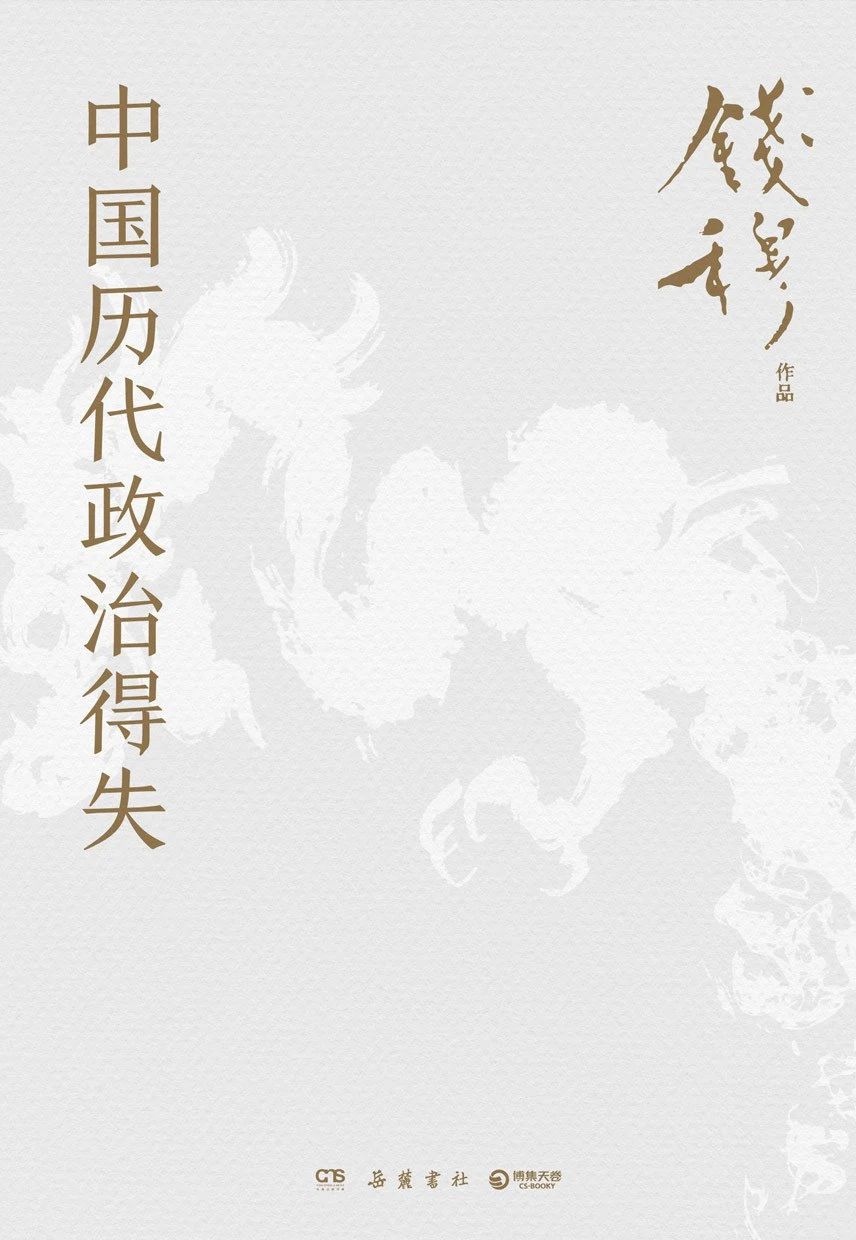
“以銅為鑒,可以正衣冠;以人為鑒,可以知得失;以史為鑒,可以知興替。”
近幾年來一直在零零碎碎地讀些歷史,感覺歷史中間自然蘊藏著它不可言說的力量。但是貿然讀史,總有一種無從下嘴的感覺:讀歷史時我們到底需要關注什么?我們能夠從哪些角度來觀察歷史?我們需要從歷史中學習什么?
正當筆者在歷史的迷宮前茫然不知所措時,錢穆先生適時出現,像一個導游,用他的《中國歷代政治得失》一書,把自漢代至清代的政治制度梳理了一遍,從政府組織、選舉制度、經濟制度、兵役制度四個方面,分析漢、唐、宋、明、清的制度利弊。王朝間的興替、興替中的傳承、傳承下的變革,儼然一幅豐富多彩的畫卷,在眼前徐徐展開。全書都很精彩,不再一一復述,只能摘出閱讀過程中筆者感觸頗深的幾個片段,與大家分享。
(注:文中加了引號的內容,如果沒有注明其他出處,那就都是引用錢穆先生在《中國歷代政治得失》一書中的表述。)
一
漢武帝把鹽鐵經營權收歸國有
商業要對自己的政治地位有清醒的認識
話說當年,漢武帝為了開疆拓土,預算不夠用了。漢武帝把自己的私房錢都拿出來了,發現還是不夠用。于是號召地方上的有錢人,尤其是收益頗豐的鹽鐵商人,給國家捐些錢,以便漢武帝能夠繼續完成自己的宏偉大業。
但是,響應者卻寥寥無幾。
漢武帝就怒了,怒的同時腦子還在線,他就想啊:你們鹽鐵商人賺這么多錢,到底是從哪里賺的呢?
“豈不是都由我把山海池澤讓給你們經營,你們才能煮鹽冶鐵,發財賺錢”,錢穆先生在書中是這么描述的,“現在我把少府收入都捐獻給國家,而你們不響應;那么我只有把全國的山海池澤一切非耕地收還,由我讓政府來經營吧!”(少府收入就是漢武帝的皇家私房錢)
于是乎,鹽鐵經營權自此收歸國有,商人們不能再擅自經營。這項制度一直傳承至今,迄今《民法典》物權編里仍然明明白白寫著,“礦藏、水流、海域屬于國家所有……城市的土地,屬于國家所有……森林、山嶺、草原、荒地、灘涂等自然資源,屬于國家所有”,屬于集體所有或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。這些歸國家所有的資源,商人們想申請經營的話,都是需要辦理行政許可手續的。
漢代的鹽鐵商們為什么會是這個局面?根本原因在于他們對自己的政治地位沒有一個清醒的認識。國家政權站在一個國家的食物鏈頂端,對一國政權中的活動享有絕對的話語權,商業活動從來不會因為自己的體量夠大,就能夠與一國政權相抗衡。
遠的不說,近的就有好多鮮活的例子,這里不再一一列舉。只能說:不論是在哪國經商,商業群體都需要有足夠的政治敏感性,以及合適的政治觀念。
二
皇權和相權的分割與制衡
分權這件事情不是西方才有
(一) 皇權中分化出相權,并相互制衡
一說到分權,我們往往把目光看向西方,提及洛克、孟德斯鳩,并對美國的三權分立制度津津樂道。但其實早在中國漢代,就有了自成一家的分權思想和制度,那就是皇權和相權的分割與制衡,以及對相權的進一步分割和制衡(漢代從秦朝傳承下來的三公制度,唐代的三省制度)。
按照錢穆先生的觀點,中國歷史上形成統一政府始于秦代,漢代則把這一制度傳承并發揚光大。而皇帝作為一國政權的領袖及代言人,他的誕生孕育了皇權這一權力形態。
但皇帝一人及皇室的力量有限,不能以一己之力完成整個國家運行管理的繁重任務,所以需要幫手來幫他打理家國事務。這個幫手從哪里來呢?
自然是“親中選賢”:秦漢形成統一政府之后,化家為國,皇帝的家臣們也一躍成為國家機構的管理人員。
基于此,漢代的各類官名,都是始于前朝歷代對家臣的稱呼:宰(內管家)、相(副手)、太常(即“太嘗”,試菜有沒有毒的)、光祿勛(看門的)、衛尉(保安隊長)、太仆(趕車的、司機)、廷尉(執行家法的)、大鴻臚(傳話的)、宗正(修家譜的)、大司農(管錢的【皇室外經濟】)、少府(管錢的【皇室內經濟】)。(這就是漢代九卿在當時的真實含義,跟“弼馬溫”之類的稱呼,沒什么本質上的區別。)
扯遠了,言歸正傳:皇帝需要從自己的家臣中選幫手來打理家國事務,并形成了政府組織。而宰相作為政府組織的首腦,就帶來了“相權”這一權力形態。
相權既是皇權的輔助,也是對皇權的制約,皇權和相權自其誕生時就自帶相互制衡的屬性,因為相權背后的文官集團的力量,也是不容小覷的,不是非常有個人魅力的君王,很難周全應對。當年萬歷皇帝因為疲于應付文官集團,索性二十年不上朝。一山不容二虎,皇權與相權在中國歷史上,開始了他們相愛相殺的旅程。
(二) 皇權對相權的兼并
按中國歷史的總體趨勢來看,皇權與相權之爭,是一個皇權逐漸集中、相權逐漸式微的過程。(這是個體在“對完整權力渴望”的驅動之下的必然產物)
這個趨勢在唐代并不明顯,那會還主要是世族大家當政,有用人的膽量和容人的氣魄。自宋朝開始,因為有了“晚唐五代進士輕薄傳下的一輩小家樣讀書人”,就開始擔心這擔心那,想把一切權力都握在皇族手中,開始吞并相權。
到了明代,朱元璋因為宰相胡維庸造反,直接就把宰相給廢掉了。但宰相的工作還是要有人去做,因為皇帝無法一個人完成,于是就設了一個內閣,也就是皇帝的秘書處;任命一個內閣大學士,也就是秘書長,來實際行使宰相的職權。
但對文官集團而言,你一個秘書長,是皇權的私人顧問,憑什么對我們政府組織指指點點的?“名不正則言不順”,即使是當時張居正這等極富才華與威望的秘書長,終因其名號的尷尬,也不得不發出“所處者危地,所理者皇上之事,所代者皇上之言”的感慨,最終被定性為“權臣弄權”,死后立馬被抄家。
清朝沿襲了明代不設宰相的制度,內閣也開始擱置,轉而設了個軍機處:皇權吞并相權的同時,順便把軍事權力也集中到皇帝手中。
至此,皇權的集中達到了史無前例的程度,平衡被徹底打破。
(三) 中間商賺差價
一種平衡一旦被打破,就勢必會有另一股力量出現,試圖重新達成一種新的平衡。皇權過于集中后,因憑大多數皇帝的一己之力,勝任皇權的治理范圍都有困難,更不用說握皇權與相權于一手。
皇帝他也需要幫手啊。原來的幫手是宰相,宰相被邊緣化了之后,宦官、外戚等與皇帝親近的人,就有了作為中間商去賺差價的機會,真真實實地獲得了一部分相權甚至一部分皇權。甚至到了明代,太監首領(司禮監)不僅成為了真宰相,而且是真皇帝。雖然明太祖朱元璋基于自身的高瞻遠矚,立下了“內臣不得干預政事”的祖訓,但卻無法保證自己的子孫后代都像他一樣勤奮、鐵血且精力旺盛。
于是乎,皇權外落,有名無實。到頭來,竟是為他人做嫁衣裳。
三
“讀書人的政府”和書籍資本
書中自有顏如玉,書中自有黃金屋
因為漢代開始用舉孝廉的制度,認認真真地選拔有學識的讀書人做官、加入國家政權組織,并且“自漢武帝以后,漢代的做官人漸漸變成都是讀書出身了”,錢穆先生把這種現象稱之為“讀書人的政府”,或者“士人政府”。
這一制度也締造了中國人民“學而優則仕”的傳統信念。到目前為止,我們政府組織中的人員,也都是以讀書人為主,大部分人員都是經過各種考試制度層層選拔出來的。這就是“學而優則仕”。
在這種制度和信念的驅動之下,舉國上下的人民都把讀書奉為一件至高無上的事情,什么“萬般皆下品,唯有讀書高”,什么“書中自有黃金屋,書中自有顏如玉”。
不過在唐代之前,這個書,不是你想讀就能隨便讀的。囿于當時造紙技術未成形、印刷技術未發明,書籍這個東西,可是很貴的。
根據錢穆先生描述,“古代書本必得傳抄,一片竹簡只能寫二十來字。抄一本,費就大了。帛是絲織品,其貴更可知。而且要抄一本書,必得不遠千里尋師訪求”。可見在當時讀書,不僅書籍成本高,獲得知識的成本也很高。(人家說的學富五車,如果以竹簡作為計量單位并換算成現在的紙質書籍的話,可能都裝不滿一行書架。據說學富五車只有“四十回《紅樓夢》的字數”,這個說法筆者沒有仔細考證,讀者朋友們不必當真。不過莊子當年是用“學富五車”這個詞來諷刺惠施的,只不過被后人用作了褒義。)
所以在紙張和印刷術推廣之前,書籍是非常重要的戰略資源。而當時雖然已經不再是爵位世襲的年代,但書籍卻是可以世襲的。于是乎,在讀書人政府的背景下,書籍和知識“變成了一種變相的資本”,并有“黃金滿籝,不如遺子一經”一說。(那個不認識的字,讀音同“贏”)
在古代中國,書籍也是一種資本。在這種書籍資本的加持下,“當時一個讀書家庭,很容易變成一個做官家庭,而同時便是有錢有勢的家庭”。所以宋真宗趙恒再勸世人多讀書時說“書中自有黃金屋,書中自有顏如玉”,放在當時的背景環境中來看,是一點也不假的。
不過說來也奇怪,宋真宗竟然把讀書的目的僅僅錨定為“顏如玉”和“黃金屋”,未免漏掉了許多讀書的樂趣。或許自有他政治宣傳的考量。
四
用人的藝術
不但要畫餅,還要能充饑
(一) 畫餅的藝術
話說唐朝初期依賴于府兵制,開疆拓土,盛極一時。后來府兵制逐漸式微,朝代也開始走下坡路。這其中的原因,拋開當時配套的經濟制度不談,我們來看看用人方面的變化。
唐朝初期,只有上三等、中三等的民戶子弟才可以當兵(唐朝根據各家財富產業,把民眾分為九等),也就是窮人家的子弟,想當兵都當不了。
每個府兵都需要去中央首都服役一年(他們叫“上番”),此間或許還能跟李世民一起練習射箭。如果戰死沙場了,中央政府收到軍隊上報的死亡名冊后,會立即要求地方政府派人去死者家中慰問,賜予勛爵和賞賜。“陣亡軍人的棺木還沒運回,而政府一應撫恤褒獎工作都已辦妥了”。
政府的這種做事方式,給了當時的軍隊以極大的精神鼓勵。所以軍隊在戰爭中屢獲勝果,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。
但是從唐朝中期開始,因為開疆拓土的任務已經基本完成,國家對精壯兵力的需求量下降,府兵上番時就逐漸怠于操練,變得無事可做。
有剩余的勞動力,自然是不用白不用。于是乎,府兵上番期間,逐漸變成皇族親貴修花園、蓋房子時借用的苦工。
這樣一來,軍人有勛位在身的同時,卻還要被喚去服力役,勛位開始轉為一種羞辱,最終演變為“別人稱呼你勛位如中尉、上校之類,已不是一種尊敬,而成了一種譏諷”,軍人的地位開始下降。
式微,式微,胡不歸?
隨著軍隊內部管理風格的散漫,對戰亡軍人的撫恤工作也開始懈怠,以至于戰事已經結束了、死者家屬已經從私下渠道得知死訊了,而官方的撫恤慰問還遲遲不來。這樣一來,在死者家屬看來,“死的似乎白死了”,人心就開始渙散。
再加上府兵制后來變成沒有復員的安排,要一輩子當兵,“歸來白頭還戍邊”。而且是做苦力、沒地位,府兵自帶的絹帛錢財還會被搶奪。以上種種原因的催化之下,府兵制最終瓦解。
看來,把“希望”與“榮譽”作為用人的激勵機制,很重要。
(二) 光畫餅沒用,還要能充饑
因為科舉制度的盛行,唐朝政權對知識分子開放后,越來越多的讀書人通過考試進入政府。當供過于求的時候,讀書人開始變成“政治脂肪”。但當時政府的思路并不是減肥,而是找地方存放這些“脂肪”。
于是乎,唐朝的地方組織結構拋棄了漢代的扁平結構,開始增加層級:把縣分上中下三級、把州也分上中下三級,這樣一來,能安排的官員就增加了。
人員安排的問題是解決了,但是弊端也隨之而來。
因為唐代的官員任用權全部集中于中央的吏部,政府只能以升遷來獎勵地方官員。在漢代的扁平結構下,縣官之上就是郡官,郡官的待遇已經等同于中央的三公九卿。這種情況下,因為階級少,官員的升遷機會優越,故能各安其事,人事變動不大,行政效率也隨之提高。
到了唐朝,光是縣官就得內部先升3級,才能實質性地往上邁一級,升了等于沒升。而唐朝的職事官有九品30級、散官有九品29階。長此以往,雖然官員一直在升遷,但“下級的永遠沉淪在下級,輕易不會升遷到上級去”。于是乎,官品中逐漸分清濁,官員與官員的地位開始有高低之分。而大批官員們也因為沒有希望、沒有動力,行政效率大幅下降。
這種狀況一直持續,待到了明朝,明成祖一句“胥吏不能當御史”、“胥吏不能考進士”,便徹底坐實了流品的弊端。于是乎,師爺這個群體愈發興盛,更從師爺唱主角的“胥吏政治”之中演化出“文書政治”(文書政治可以大約理解為:無字無真相,書面文件是第一生產力)。
行政環節中的各種繁文縟節、看不到希望的濁流群體的自暴自棄,一直在影響著行政效率,不停地制造問題(“流品”就是官階,把官員分成優等和劣等,后來泛指人的社會地位、門第)。果真是,壞的制度讓好人不能做好事。
可見用人這件事情,光畫餅是不行的,畫的餅還得能夠充饑。不然,勞動者們醒悟過來只是遲早的事情。至于想靠畫餅收割短期勞動力的,另說。但那有損用人者的風評,終究不是長久之計。
五
監察常駐
中央和地方的微妙關系
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向來都是微妙的,需要謹慎平衡。
(一) 中央與地方的角逐
中央對地方管得太死了吧,地方失去了自身發展的活力,中央也累得慌,根本管不過來。中央管太松了吧,地方就開始肆意妄為、欺上瞞下,甚至占山為王,向中央權威挑戰。
為了解決這個問題,歷朝的通用做法是向地方派出監察人員(監察制度這個事情后面還要細說),并完善地方與中央的信息溝通機制,建立固定的地方信息上報制度。古代的修驛站、修官路,就有加快中央與地方間信息傳遞速度的考慮。
到了元朝,更是從地理的角度出發,把各省的地理界線劃分得彎彎繞繞的,就是刻意把重要的地理防御工事分布在2個省、3個省甚至更多省份之中,防止其中某一個省依賴地理優勢,難以被攻克。用錢穆先生的話說,“好使全國各省,都成支離破碎。既不能統一反抗,而任何一區域也很難單獨反抗”。(插播一句:行省制度是元朝開始啟用的)
后代統治者自然明白元朝對地方行政區域劃分方式的良苦用心,就傳承了下來,并且一直沿用至今。不得不說,元代統治者對地理知識的嫻熟運用,值得我們學習。
而元朝統治者對地理知識的重視,恐怕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宋代的慘痛教訓:
北宋定都河南開封,黃河邊,一大片平地。“騎兵從北南下,幾天就可到黃河邊。一渡黃河,即達開封城門下”,完全沒有國防(自然,宋太祖這么做決定,有他的苦衷:當時承接五代十國的混亂局面,國防線早已殘破。宋朝需要養兵,養兵則需長江流域的糧食供給。如果定都洛陽或西安,運費太高了,國家財力負擔不起)。
再加之開國宋太祖的弟弟宋太宗,兩次對遼親征都打了敗仗,在這種沒有國防的地理設定之下,宋朝不得不做好隨時應戰的準備。所以只能養兵,不能裁兵,還不能讓軍隊復員。但同時,憚于祖先戰敗的慘痛教訓,一朝被蛇咬,宋代也不敢再和北方遼國交戰。最后養兵而不敢用兵,開銷過大,最終死于積貧積弱。
看來,地理學知識的運用范圍,比想象中的更廣泛。扯遠了,回到中央對地方的監督制度。
(二) 監察常駐的危害
自秦漢以來,監察制度就已經是一種常態化的中央對地方的監督制度,旨在監督中央指令在地方的執行情況,畢竟天高皇帝遠。另外一個重要考慮就是中央集權,不想讓地方的權力過分強大。
漢代設的中央特派員叫“刺史”,唐代的叫“監察使”、“觀察使”(派去邊疆的叫“節度使”),宋代的叫“監司”,明代叫“總督”、“巡撫”,清代叫“經略大臣”、“參贊大臣”。
那么問題來了:為什么每個朝代的中央特派員,都要換一個名字?是因為改朝換代了,中央特派員的名字也需要標新立異嗎?事情沒有那么簡單。
其實,唐代也是有漢代“刺史”的,而宋代也有唐代的“觀察使”,清代也有明代的“總督、巡撫”。那為什么不繼續沿用上一個朝代的職責呢?因為上一個朝代派出的中央特派員,隨著時間的推移,無一例外地都成了當地的行政首腦。漢代的特派員“刺史”,在唐代已經是一州的行政首腦,唐代的監察人員“觀察使”是宋代的地方行政首長,明代的特派員“總督、巡撫”到了清代,也成了地方行政首腦。甚至唐代派往邊疆的節度使,慢慢地也成為了邊疆地區的首腦,自立山頭,形成藩鎮割據的局面,引發動亂,最終把唐朝消滅。清代也是如此。
為什么歷史總是如此驚人的相似?因為監察人員作為中央特派員前往地方時,本身是帶著至高的權力去的,因為他代表的是中央。既然欽差大臣來了,那地方遇到重要的事情,就得向欽差大臣匯報,并最終聽欽差大臣的指揮。監察員一旦在地方駐扎的時間長了,這種自帶的更高權力就會影響到地方的既有權力格局。久而久之,中央特派員就逐漸成為了地方的行政首腦。如果讓中央特派員掌握地方軍權,就更要命(請自行代入唐朝和清朝)。
一旦中央特派員成為地方首腦了,利益格局就變化了,最初的監察職責也就名存實亡,所以后朝只能再派新的中央特派員。如此循環往復。
由此可見,中央對地方的監督機制,是需要經過精妙設計的。反觀現在,監察人員要輪換值班,國企中的委派監事不能連任,多多少少有這方面的考慮。
六
文官武官,終歸田園
農村大后方對國家政權穩定的保障
歷代“學而優則仕”的傳統,是不曾斷絕的。但是仕途有通暢就有不暢。仕途不暢時,官員們該去往何方呢?
陶淵明說,田園將蕪胡不歸?“中國歷史上的經濟與文化基礎,一向安放在農村”。大不了回家種田,是寫入中華文明基因里的觀念。所以我們常常看到,歷代文官仕途不順時,往往會請辭:回家種田,做個小地主,對外可以稱之為“衣錦還鄉”。唐朝的武官,因為空有勛號而無實職,除了在當朝做大將軍的,剩下的也多是回家種田。有知識或有武力值的官員們在失意時有了情緒出口之后,就不會惹出太多幺蛾子。
基于中華文明的這種經濟與文化基因,農村大后方在國家政權穩定方面,也一直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。根據溫鐵軍先生的觀點,農村作為一個吸納城市剩余勞動力的場所,在國家面臨經濟危機時,是一個重要的緩沖地帶,并給國家度過經濟危機提供人力、物力、財力的支持,從而使局面趨于穩定。
所以國家為什么歷來重視三農問題,是有原因的。
七
藥以治病,亦以起病
不忘初心很重要
(一) 九品中正制的興與敗
話說東漢末年,漢獻帝逃亡,中央與地方失聯,察舉制這一人才選拔制度也失去了施行的機構基礎。于是朝廷用人時便失去了標準,文人領域還尚可控制,武人領域一片混亂,用人全憑在位者的喜好,良莠不齊。為了解決這一混亂,曹操任命陳群改革人事制度。陳群不負重任,基于當時的局面,創設了九品中正制。
所謂的“九品”,就是把人才分為“上上、上中、上下/中上、中中、中下/下上、下中,下下”九個層級。那么,由誰來做這個分類的工作呢?那就是“中正”(既中立又公正,才能擔此重任)。
那這個“中正”又是怎么產生的呢?還是采用察舉制的老方案:“就當時在中央任職,德名俱高者,由各州郡分別公推大中正一人”,也就是在各地方挑選一位他們在中央任職的、德行和名望都很高的官員,擔任“大中正”。然后“大中正”再指定一名“小中正”,兩位中正就負責他們所在地方州郡的人才評分工作。
評分標準有兩個:一是能力,二是品行。被評價的對象:不僅包括未入官場的人員,也包括在職官員,旨在撤掉當時已經濫用的在職官員。評分的主要依據:地方的群眾輿論和公共意見(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)。
打完分之后,中正就把評分冊子上交吏部,吏部根據這套評分冊子,再來決定在任官員的升遷、在野人才的聘用。這樣就建立起了一套相對客觀的評價標準,解決了之前用人混亂的局面。這一套用人制度,對曹家初步統一天下是有所助益的。
但何以這一前朝治病的良藥,成了后朝致病的毒藥呢?因為每一種制度的施行,都對人們的后續行為有引導作用。
我們不妨再回過頭去看看這個制度:
1. 中正對人才評分的標準是群眾的意見,也就是“輿論”。而群眾的眼睛當真是雪亮的嗎?至少勒龐并不這么認為。
在《烏合之眾》中,勒龐的觀點是,群體只有形象思維,缺乏邏輯推理能力,“不能辨別真偽或對任何事物形成正確的判斷。群體所接受的判斷,僅僅是強加給他們的判斷,而絕不是經過討論后得到采納的判斷”。這一觀點讀者們是否認同,暫且不論,我們且來看看當時的人們在這種制度的引導下,做出了什么行為:
因為人才評價重社會輿論,做官的人就“襲取社會名譽,卻不管自己本官職務與實際工作”。因為人才評價機制在于聽取社會輿論的“中正”,而真正了解官員業務能力及人品的上司,卻無法把他們對下級官員能力與德行的評價發布出去。后果可想而知:慢慢地,官員們會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花在經營自己的對外“人設”上。至于他的本職工作做得如何,沒有人關心,也沒有人知道;知道的人也難以把他們的觀點擴散。
2. 大中正這個職位設在中央,而人才們想要大中正品題提拔自己,就紛紛往中央的大中正身邊靠攏(所謂“認知”,要先“認”,才能“識”)。如此一來,人才紛紛往中央集中,地方缺乏人才可用,并導致地方的行政效率、風俗易化的腳步,都慢了下來。
至此,九品中正制已經完全異化,不僅不再具有其初設時分清定濁的作用,反而給人才選拔帶來不便,給世人的行為舉止產生的不良的引導,最終被后世唾棄,并被唐朝的科舉考試制度取代。
之所以有這種局面,就是因為后朝沒有去思考前朝推行這一制度的背景和原因,在時代背景變化之后仍然一味沿用,終致當初“治病之良藥”,變成了現在的“致病之毒藥”。
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。
【想起一個小故事:軍營操場中的某把鐵椅,常年以來都有2名士兵把守,但不知原委,都是奉命行事。一日,退休的長官到訪,見到這把椅子依然有人把守,便問左右隨同:30年了,這把椅子上的油漆還沒有干嗎?】
(二) 從“租庸調”到“兩稅制”
無獨有偶,唐代的稅收制度,也經歷了從“良藥”到“毒藥”的轉變。
唐初為了從戰亂中恢復元氣,輕徭薄賦、為民制產,推行“租庸調”的稅收制度,讓有恒產者有恒心。這是一種計劃經濟時代的屬人稅收制度:
所謂“租”,你可以大致理解為“土地承包制+農業稅”:土地的所有權歸國家,人丁年滿18歲時官方授予他一定面積的田地;滿60歲時把田地交換國家。耕種期間,每年按2.5%的稅率(四十稅一)向國家繳納農業稅。
所謂“庸”,是一種力役,每個成年人丁每年向國家提供20天的義務勞動。
所謂“調”,是一種特產稅,各地人民每年需要向中央貢獻一定量的當地土產,以絲麻織物為主。
這一套制度下來,形成了“有田始有租,有身始有庸,有家始有調”的格局,旨在為民制產,達到“有恒產者有恒心”的目的。而按人頭分配一定面積的田地,也具有一定計劃經濟的屬性,試圖通過“均田地”實現“天下大同”(大約可以理解為我們現在倡導的共同富裕)的終極政治理想。
那么這一稅制的實施效果如何呢?
既然要屬人管轄,租庸調這一稅制的根基,便是人口戶籍管理制度,他們當時稱“賬籍”制度。“賬”是壯丁冊,一年一刷新;“籍”是戶口冊,三年一刷新。也就是在唐代,每1年要做一次壯丁普查,每3年要做一次全民人口普查。人口普查這件事情,在數據和技術均完備的現在,開展起來尚是紛繁復雜;那在車馬皆慢的唐朝,其難度可想而知。而人類這個物種,往往是喜歡偷懶的,時間久了就開始懈怠:年過60的壯丁不銷戶,滿18歲的新丁沒增名,已經去世的人沒有及時從戶口本中刪除,新授予的田地沒有及時修改權利主體……更有地方豪強從中舞弊、阻撓制度施行。如此種種,最終導致戶口登記逐漸錯亂,“賬籍”制度無法推行,并成為租庸調制失敗的最大原因。
對此,錢穆先生總結的應對之道是:“每一項制度之推行與繼續,也必待有一種與之相當的道德意志與服務忠誠之貫注。否則徒法不能以自行,縱然良法美意,縱是徒然。”
所以,歷代王朝為何推薦儒家/法家/道家思想,各種組織為何強調統一思想,各家企業為何建立企業文化,每個家庭為何開展家風建設,都是同樣的道理。人類喜歡聽故事,人類也需要聽故事。
租庸調制失敗后,兩稅制開始登場,并開啟了唐朝的自由經濟時代。
所謂“兩稅”,就是兩次征稅:夏天征一次,秋天征一次。與租庸調制不同,兩稅制是一種屬地的稅收制度:誰在這片土地上居住不重要,把該交的稅交上來就行。這樣一來,人口不再受戶口的牽制,人口流動變得自由。
但這自由的代價,便是土地兼并:之前的租庸調制是按人口分配田地的,現在田地不按人頭分配了,土地的流通就是可以允許的。而歷朝歷代的土地兼并,最終的后果總是貧者愈貧、富者愈富,最終導致地方割據、各占一方(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)。唐朝也不例外。
隨著實施時間拉長,兩稅制還出現了另外一個弊端:最初將租庸調改兩稅制,還有簡化手續之考慮,把原來的3個稅種放入土地中一并征收。但是慢慢的,主政者就忘了當初的那個設定,忘了初心,覺得稅收不夠用時,又巧立名目,新增征稅項目。“而這些新項目,本來早就有的,只已并在兩稅中征收了;現在再把此項目加入,豈不是等于加倍征收!這是稅收項目不分明之弊。”這樣一來,民眾的稅賦自然就重了。
再者,兩稅制采屬地管轄,稅基按該政策出臺前一年的稅收金額來定,后續不再調整。不管這個地區人口多寡、年度收成好壞,都要交固定金額的稅。稅收“變成了一種硬性規定,隨地攤派,而不再有全國一致的租額和稅率了”。如果某一地區某年收成不佳,或者其他偶發原因導致經常居住人口減少,在稅收總額不變的情況下,剩下居民的稅賦就會加重。而單位數量人口的生產力是有限的,稅賦一重,居民負擔不起,就會往稅賦低的地區遷徙;如此一來,剩下居民的稅賦會更重。循環往復。
此外,唐朝兩稅制不是納糧,而是納銀(貨幣)。農民必須賣糧換錢,用來交稅。有交易,就會有中間商賺差價。最終被市場調節的,還是底層供貨商——農民。
因為有這些弊端,兩稅制的推行,失去了“為民制產”的初衷,引發土地兼并和貧富不均,而且實質上是在獎勵地主的剝削,最終為唐朝末期的農民起義埋下了禍根。
八
興替間的傳承
現有制度中的歷史厚重感
在閱讀歷史的過程中,我們是可以感受到現有制度中的歷史厚重感的。中國古人的傳統智慧,仍然在指導著我們現在的生活。這里難以列舉齊全,稍微舉一些例子:
(一) 按各區人口比例,分配人才的錄用名額
從漢代開始,人才的選拔制度便是分區定額的:根據各地區人口基數的不同,分配不同比例的人才錄取額度。為的是平衡各地區的利益,聽到各地區的聲音。這個制度,一直沿用至今,具體體現在高考時各省的錄取人數、以及因此形成的各地高考難度不一的現象。
(二) 聯席會議制度、聯動辦公制度
唐朝的三省因相互制約,一道政令出臺前需要三省交叉審核。為了提升行政效率,政府需要制定行政命令時,門下省和中書省便會舉辦聯席會議,共同審核政令。這一制度也沿用至今,且廣泛存在于政企的各部門協調工作之中。
此外,唐朝六部因共有24司,為了實現協同辦公,每天上午各部主管都在都堂集體辦公。這可能是我們現在政府各部門聯動辦公的原型。
(三) 公務員不得經商
漢朝就規定,商人不能做官,做官人不能經商。到了唐朝,直接從報考資格開始限定:工商界人士不能參加科舉考試,“因為商人是專為私家謀利的,現在所考試求取者則須專心為公家服務”,更不能有犯罪記錄。這就是所謂的“身家清白”。這一制度也是沿用至今,公務員不得經商。
另外,還有前兩篇提到的國家對特定行業的專營制度、學而優則仕的傳統、各省行政區域的劃分、監察制度、三農政策、戶籍制度、人口普查制度等等,都是傳襲于唐漢甚至更早的年代。再如宋代的匿名評卷制度、元代的中央特派員制度、歷朝以來形成的文書政治、士人政權的傳統,都對我們現在的生活產生著深遠的影響。傳統文化中的智慧,是值得我們學習并發揚光大的。
九
以歷史的眼光看待歷史
成年人不應回過頭嘲笑蹣跚學步的孩童
錢穆先生歷來主張以溫情的眼光去看待歷史。“制度決非憑空從某一種理論而產生,而系從現實中產生者。惟此種現實中所產生之此項制度,則亦必然有其一套理論與精神。理論是此制度之精神生命,現實是此制度之血液營養。”
任何一項制度的產生,都是基于當時的實際情況和現實土壤,都是為了解決當下的問題。如果不代入當時的現實環境,而是以后來的眼光去評價一項制度的得失,是不合適的(這也是“事后諸葛亮”不招人喜歡的主要原因)。
作為一個成年人,在學會了走路之后,如果再去嘲笑孩童時的蹣跚學步,也是不合適的。當然,根據制度制定者的前瞻性、周全性、經驗豐富程度的差異,不同的制度本身依舊有其優劣之分。
筆者只能說:前世之事,后世之師。
作者簡介
李芳
國浩深圳合伙人
業務領域: 建設工程與房地產、投資與并購、民商事爭議解決
郵箱:lifangsz@grandall.com.cn

